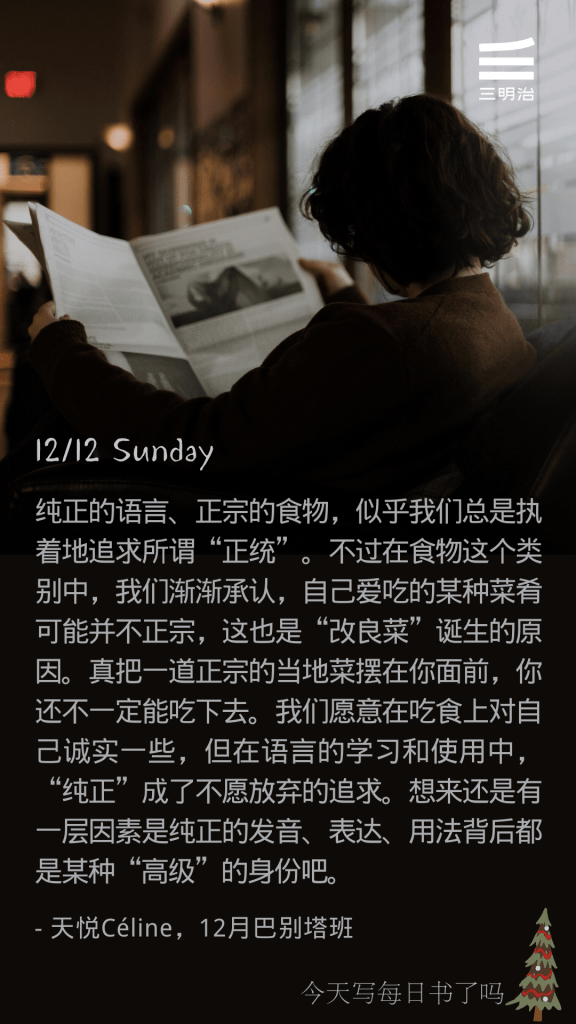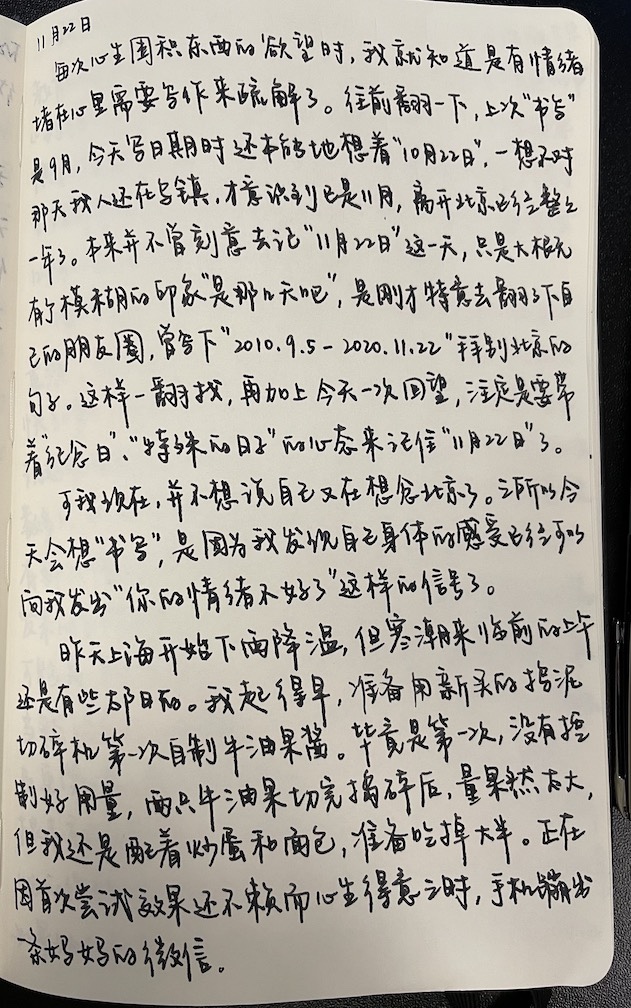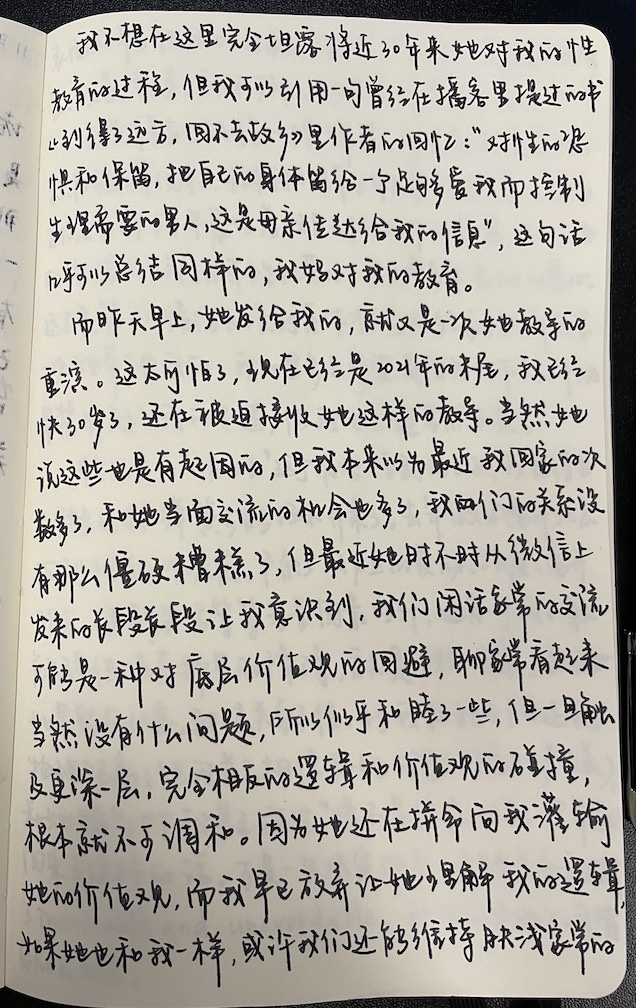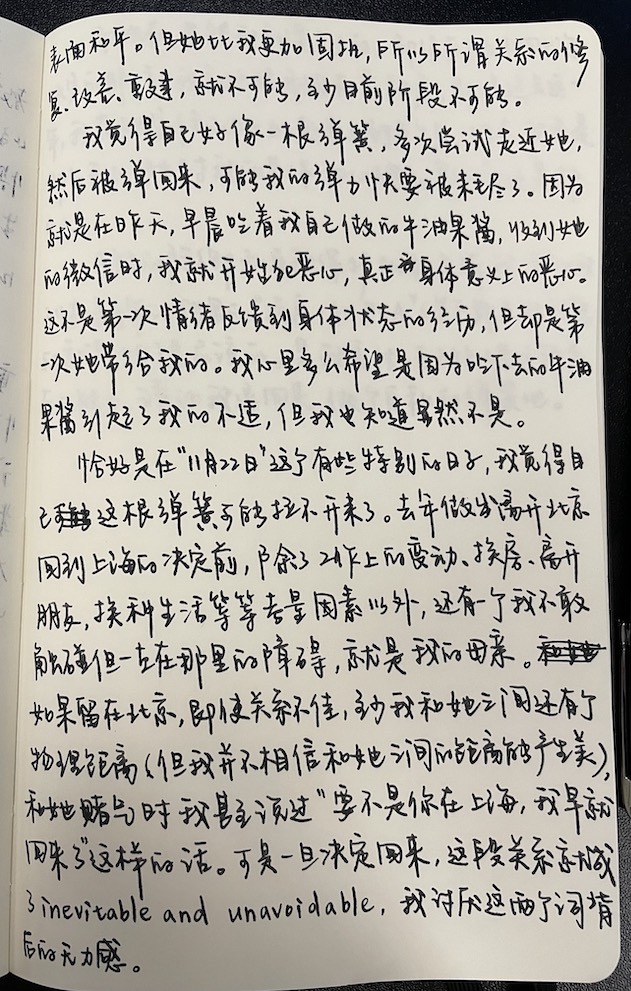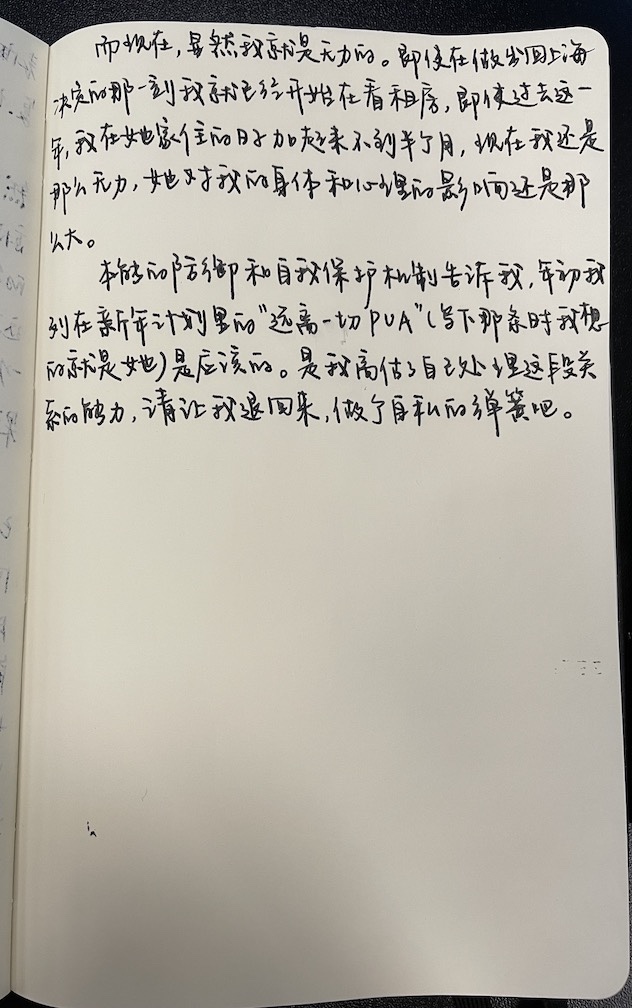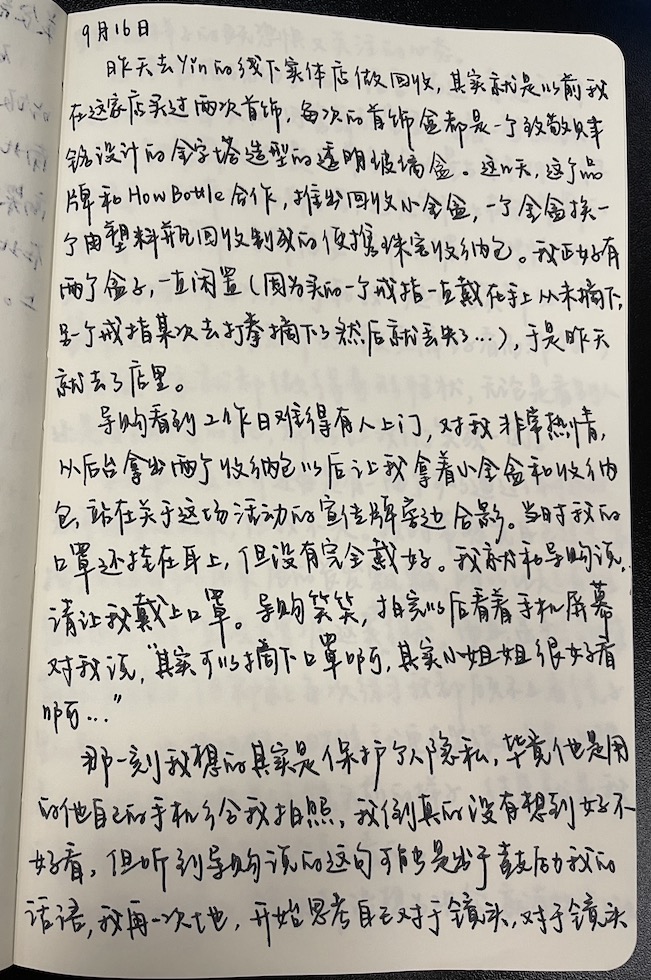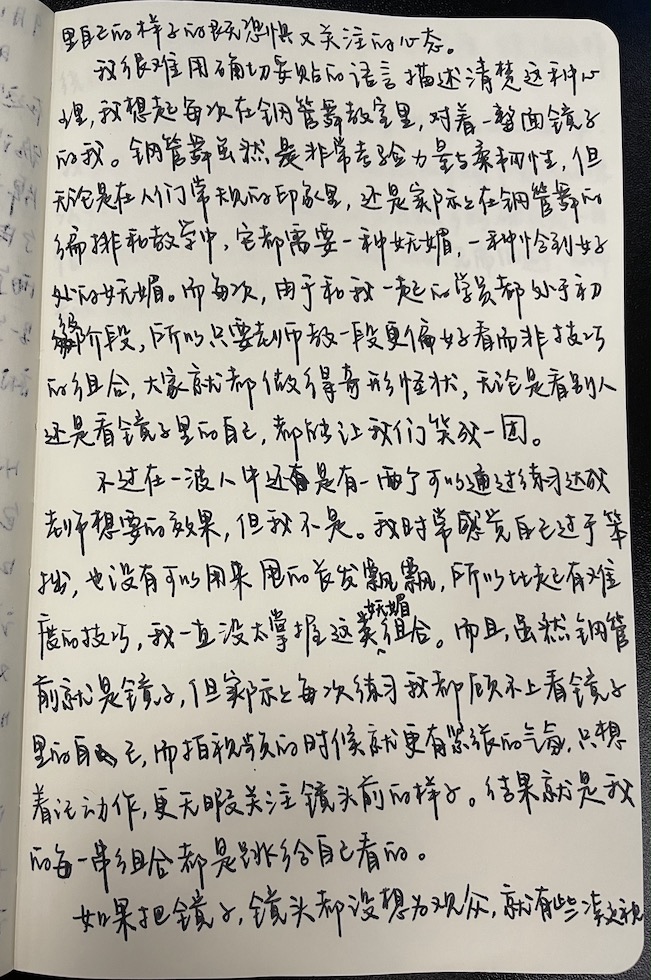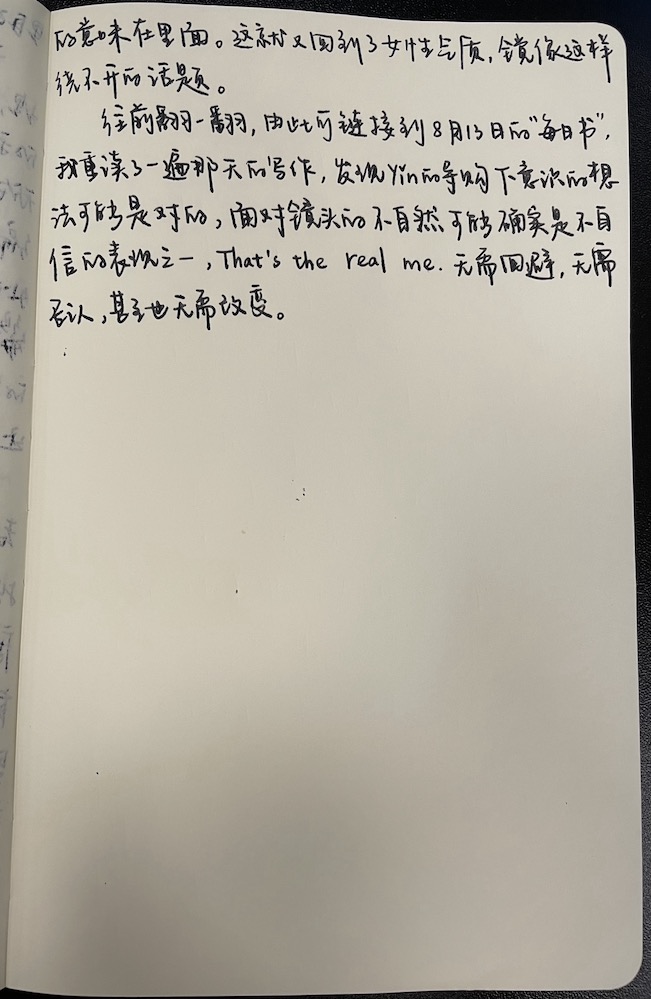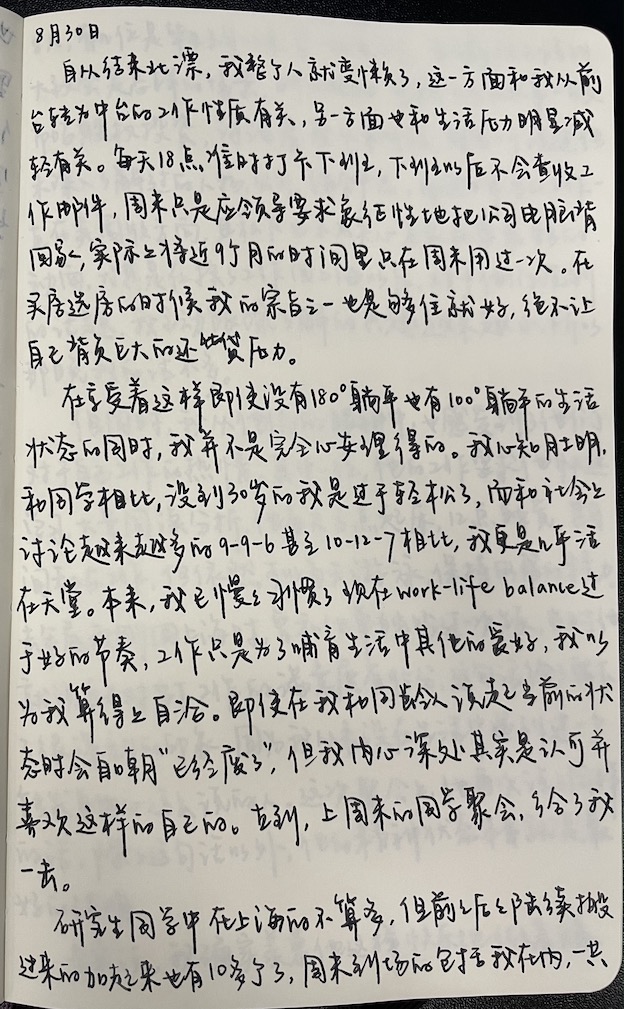回上海以后,月经一直不规律,做了各种检查确定子宫、卵巢、乳腺、甲状腺都正常,也就是说没有相关的器质性问题。可我现在生活作息规律,不焦虑也没多少压力,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过痛经,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运动次数和强度也绝对达到甚至超过女性的平均水平,现在的工作也不用喝酒了,即使是换城市导致的水土不服,一年半也该缓过来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去过几家三甲医院,西医说不出来啥,最多给我开点激素,中医看了我的化验单,说某某指标在正常范围内,但还是偏低噢,然后问我:“你想吃中药么?”当下我有些懵,感觉对面的她也没觉得这是件需要吃药的事,就是一副“你想吃点药调理调理也行,不吃也行”的态度。确实,如果是以前的我,可能真的不会太在意,甚至感到无比自由。子宫内膜的脱落有快有慢,量也有多有少,周期28天和周期40天都是正常的,而我就是周期更长一些。影响月经的因素实在太多,只要能确定没有病理性因素就好,但最近这件事开始困扰我。
这个年龄段的朋友之间聊天,常常聊到结婚怀孕这件事,说起身边人的案例,免不了都是惨痛的类型(大概是因为只有惨痛案例才是有头有尾可以讲出来的故事,而不惨痛的案例就被视为正常,并不会说起),这样的“幸存者偏差”就导致我现在听到的看到的全都是在生育方面这样那样的痛苦。甚至有朋友表示,不希望生女儿,因为儿子将来无需经历这一切。从备孕,到怀孕,再到分娩,每一步都可能有各种bug。而我现在的状态,可能会是一种隐患。
站在自然原始的角度,只有女性有子宫这个器官,只有女性能生孩子。抛掉“在我国只有结婚才能生子”这一制度性的人为限制,28周岁的我现在的身体状态就是适合怀孕分娩的。willingness和ability是两个概念,即使我这辈子都搞不清楚“想不想生”、“要不要生”的无数个问题,我都不想失去生育的能力。
所以我现在每天早晚都在喝中药。
我的阿姨在不到40岁时查出子宫肌瘤,切除了子宫,当时她女儿也就是我姐姐在上初中,我在上小学。阿姨在红房子医院做完手术以后,我们去看望她,不知为何,医院没有让我们两个小孩子进去,所以一个同行的远房亲戚留在医院门口陪着我们姐妹俩,姨父、妈妈、外婆等亲近的家人进病房探望(这大概也是我后来再也不想踏进红房子医院的缘故,即使它是我国历史最悠久、技术水平也有保证的妇产科医院之一)。我永远记得,妈妈从医院出来时,以及自那以后妈妈时不时说起的,还有阿姨几次亲口对我说起过的,切除子宫,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是多么难受的事。即使她已经生过孩子,即使按照当时的制度也不可能再生一个。
阿姨切除子宫的时候,我还没有月经初潮,对于自己女性的身份其实是没有概念的。月经初潮以后,青春期的我每次月经量都很多,又因为没有经验,更是从来没有接触过除了卫生巾以外的其他神器,经常弄脏裤子和床单被单。妈妈安慰我,小姑娘头几年月经多是正常的,又对我说,你看阿姨没有了月经,脸色都暗沉了不少,毕竟少了每个月的排毒啊(这一点我现在是不相信的,月经只是一层膜的脱落,不排毒不排毒真的不排毒)。
从阿姨和妈妈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女性对于子宫这个代表了fertility的器官的留恋和失去它的遗憾。
从月经初潮到围绝经期结束,女性的命运都围绕着月经和分娩。过去我总觉得,月经意味着拥有分娩的能力,可以成为生育的工具,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慢慢地我开始意识到,即使这项能力给她带来了那么多潜在的痛苦,也没有一个女性愿意失去它。妈妈围绝经期的阶段,我没有陪在她身边,现在当面说起,她只是轻描淡写的“我没啥,身体没有作天作地”一笔带过,我从来没有深入和她探讨过当时她的身体状态和心理波动。我也是近一两年才了解到,医学上“围绝经期”的概念比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更年期”的含义更广,因为它是一个时间跨度可能长达十多年的阶段,绝经只是其中一种临床表现,期间还可能会发热盗汗,会高血压,会焦虑易怒,总之就是浑身上下都不痛快。而在大众的叙事中,这些不痛快都是正常的,男人会说“你妈更年期,离她远点”,老人会说“过了就好了”,甚至正在经历这个阶段的女性自己都不会把这些身体和心理的不适挂在嘴边,有什么好说的呢。就像怀孕生孩子,痛苦都是正常的,生完孩子睡不好觉、尿频甚至漏尿,都是正常的。又不是独独你一个。
Fleabag第二季里最动人的一段是一位年长的女性对Fleabag说,更年期以后的女性终于自由了。No longer a slave, no longer a machine, with parts. You are just a person in business. 这是一种态度。当然也还有另一种全然相反、不愿老去的态度,可能还占多数。没有亲身经历的我,只能通过文艺作品里的些许段落和身边长辈的只言片语,对那个比青春期更加漫长的生命阶段做单薄无力的想象。她们,也是未来的我们,究竟在经历什么呢?
附上Fleabag台词,给未来的我们一抹黯淡的亮色吧。
Women are born with pain built in. It’s our physical destiny. Period pains, sore boobs, childbirth, we carry it within ourselves throughout our lives. Men don’t. They invent all these gods and demons and things just so they can feel guilty about things, which is something we also do very well on our own. And then they create wars, so they can feel things and touch each other, and when there aren’t any wars they can play rugby.
And we have it all going on in here, inside. We have pain on a cycle for years and years and years and then, just when you feel you are making peace with it all, the fucking menopause comes and it is the most wonderful fucking thing in the world!
And yes, your entire pelvic floor crumbles and you get fucking hot and no one cares, but then… you are free.
No longer a slave, no longer a machine, with parts. You are just a person in business. I was told it was horrendous. It is horrendous, but then it’s magnificent. 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to.